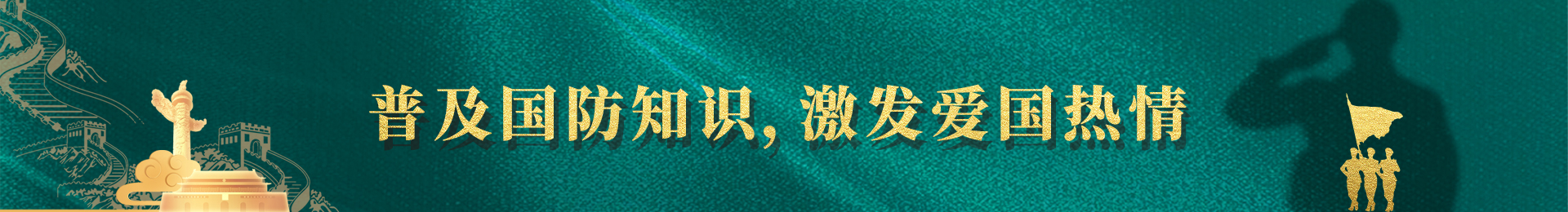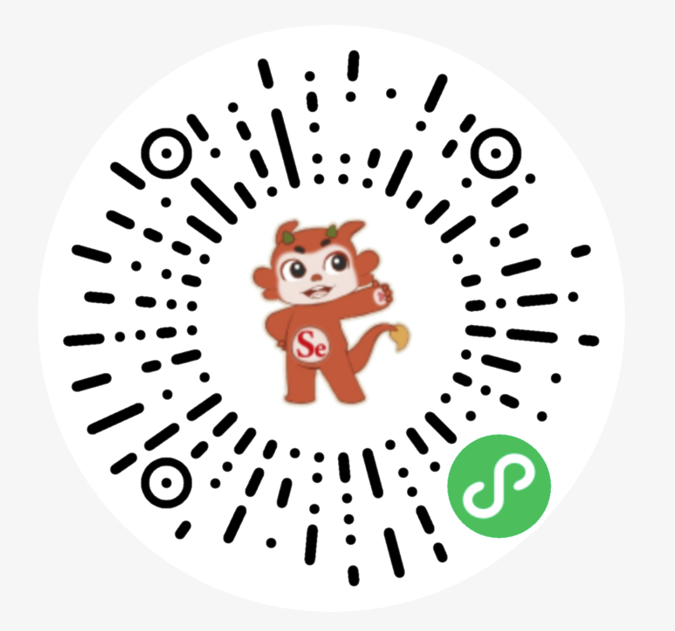协会地址:苏州市虎丘路88号
要点导读
●胡主席强调指出,要坚持把发展新型作战力量作为战略重点。新型作战力量是先进技术和新型作战思想联姻的产物,是带动军事实力整体跃升的引擎,也是新军事变革完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国际战略大博弈中,地位向来举足轻重。
●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是一项探寻“新大陆”的漫漫远征。远航,离不开眺望。但选择在哪根桅杆、向何处眺望,反映了我们当下的认知水准和力量、资源准备。发展新型作战力量,需要我们跳出传统思维的窠臼,紧扣战略需求的演变,清醒认知未来战争大势,从顶层设计入手,遵照“路线图”的方法,扎实推进管理创新,走出一条与新型作战力量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相适应的发展道路。
●发展基点:
从“追踪前沿”到“抢占高点”
历史上每一次军事变革,都是以新型作战力量的兴起为发轫。而军事变革的标志,常常伴随着新型作战力量对传统作战力量的决定性胜利。拿破仑横扫欧洲,是炮兵和散兵线战斗方式对传统军阵战斗的胜利;希特勒装甲部队闪击欧洲,是机械化军团对步兵军团的批判;海湾战争则是信息化作战力量对机械化作战力量的胜利。
新型作战力量总能赢得对传统力量质的优势。在1940年攻击法国的战役中,古德里安编组的机械化军团总人数还不到德国总兵力的8%,但他们创造了奇迹。仅仅投放了两枚原子弹,美国就迫使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从而大大加快了二战结束的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都高度关注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把它们视作维护国家安全的根基。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正是由于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新型作战力量的发展,才使得中国成为国际“大三角”的重要一极,赢得了战略主动权。
当前,我军建设两个“不相适应”的矛盾仍很突出,破解矛盾的突破口之一就是大力推动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应该看到,我军与发达国家作战力量建设的差距主要是“技术差”而不是“时代差”,这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提供了基础保证。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战略性产业的蓬勃兴起,也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提供了资源保证。能否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期积极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关乎国家安全战略全局,影响和决定着军队未来。
●发展思路:
从“基于任务”到“基于威胁”
美国军事家马汉认为,对于一个国家的战略实践来说,应有“短期性的迫切需要”与“长期性的观念”。作战力量特别是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必须在“短期性的迫切需要”与“长期性的观念”,也就是当前任务与未来威胁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二战后,美苏均以对方为假想敌,以大规模核战争为背景发展军事力量。60多年时间内,两国先后近百次对外用兵,使用的却是常规武器、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与其他国家作战。以至于伊拉克战争时,美国精心打造的数字化机步师因为“太重”,根本到不了战场。美军折兵越南、前苏联兵败阿富汗,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基于任务”的建设模式存在着很大的局限。
着眼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无疑要把关注的焦点从“和谁打”“在哪打”,转移到“打什么仗”“怎样打仗”上来。腓特烈大帝在《战争通则》中曾经询问自己:“如果我是敌人,我会制订怎样的战略?”作战对手可以变化,但作战方式却可以预设。苏联卫国战争前夕,朱可夫提议根据德军进攻波兰的特点,对苏联红军进行重组,他强调:“我不知道德军将要行动的计划,但是根据对情况的分析,他们只能这样,而不会有别的做法。”正是这种对敌手与战争形态的深刻认知,牵引着苏联红军沿着德军先行探索的机械化战争模式开始改革。无视未来威胁,无疑就会失去未来。即使在偷袭珍珠港的成果已经验证了航空母舰的强大威力,但日本人随后仍然大力发展大型战列舰,结果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受了灭顶之灾。
“我们不得不停止想明天,而去想后天。”美国各军种早在世纪之初就将军队建设的目光投向2020、2030甚至2050年的战场。而在其中表现最活跃的,是军事理论创新和作战实验论证。这实际上是在头脑中、纸上和计算机里组建了无形的作战力量,一旦需要,就可以将它们物化出来。
●发展模式:
从“项目突破”到“工程建设”
好比盖一座房子,总是先有头脑中的规划,再有图纸上的设计,最后才有工程上的施工。作战力量也有设计中、发展中和使用中的3种形态。美军将这3种形态定义为目标部队、过渡部队和传统部队。今天的“目标部队”就是未来的“传统部队”。
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一支“目标部队”,无疑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一方面,发展新型作战力量涉及面广,包括军事思想、编制体制、战略战术、武器装备、人才建设、综合保障等等,需要集纳军事专家、技术专家和系统工程专家等相关领域的智慧和成果,以确保问题研究多维视角的完整性。单项要素的突破并无太大实质意义,而结构的缺失则可能造成未来战场的溃堤。另一方面,发展新型作战力量进程长,需要妥善处理社会进步与军事需求、近期急需与长远发展、战术性调整与战略性推进的关系。特别是新型作战力量的发展是动态过程,需要在整个进程中不断调控,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持续推进。再加上,我们对未来的未知远大于已知,新需求、新知识、新经验不断涌现,也将会改变我们对未来战争和未来作战力量建设的认识。只有针对不同阶段、不同问题的特点和状况,统筹协调好各方面的建设,才能克服各自的局限性。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不仅需要改变军事制度,而且需要在更大程度上改变民政方面的整个制度。”发展新型作战力量是一项“复杂的巨系统”工程,意味着作战力量的能力重塑、结构重组和制度重构,需要引入全新的管理模式,系统科学无疑是最佳的方法论。正如钱学森所指出的,“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和使用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对所有系统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
●发展方法:
从“远景规划”到“按图施工”
随着现代管理学理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用“路线图”的方法推进复杂的工程建设。美军围绕实现《2020年联合构想》,先后颁发了《防务计划指南》《转型计划指南》和各军种《转型路线图》,把具体的发展规划逐一细化、分解到每一个技术领域、每一个时间节点。各种路线图虽然在应用范围和时间跨度上各不相同,但都体现需求和可能的统一,并整体协调目标愿景、发展思路、需求分析、重大项目、发展路径和配套措施等相关问题。无疑,明晰的发展“路线图”,可为我们提供战略设计的蓝图、战略实施的依据和战略评估的标准。
但制定“路线图”,一个常常被提及又常常被忽略的问题,就是战略过于“理论化”,战术过于“理想化”。有效落实路线图,真正发挥其指导和规范作用,比制定路线图意义更大、难度也更大。发展新型作战力量,不仅要有一张绘制好的“施工图”,更要提高“按图施工”的战略执行能力。
“天下纷扰,必合于律吕”。提高“按图施工”能力,需要军事制度创新。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美国早在二战时就认识到联合作战需要统一指挥,但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就是各搞一套太平洋战略,连总统罗斯福也难于平衡。自1958年推出《国防部改组法》,到1986年制定《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取消了军种在联合指挥中的指挥职能,经过28年美军才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正是这个体制才使得不同美军的不同作战力量真正联合到了一起。
提高“按图施工”能力,需要军事结构创新。坦克在英法军手里,只是“移动的碉堡”,在德军那里就成了开疆拓土的利器。马克斯·布特考察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海战,发现中俄两国的新型战舰远比日本多,但都将其与旧式战舰混编在了一起,使得新型战舰根本无法发挥威力。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如果不进行必要的结构重组,只在原有框架中不断进行“技术叠加”,恐怕难以释放其固有的效能。
提高“按图施工”能力,还需要军事机制创新。需要建立权威的领导机制,协调处理决策、咨询和执行系统之间的联络,监督执行落实情况。需要建立稳定的运行机制,实现人力、物力、财力向有益于战略执行的方向流动,确保能按时间节点、按标准要求推进建设。需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使长远战略、中长期规划、近期计划和年度安排纵向相联,各军兵种的发展战略、规划、计划、方案横向相通。需要建立灵敏的反馈机制,通过相对独立的执行评估,使上下间能纵向监控,各单元能横向调控,各岗位能自我管控,及时反馈信息,纠正执行偏差。
正如杜黑所言:“死抱着过去陈旧的东西不放对未来没有什么教益,因为未来跟过去发生的一切根本不同。对未来必须从一个新的角度探索。”发展新型作战力量,需要我们选择新的发展路径,用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新的办法积极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