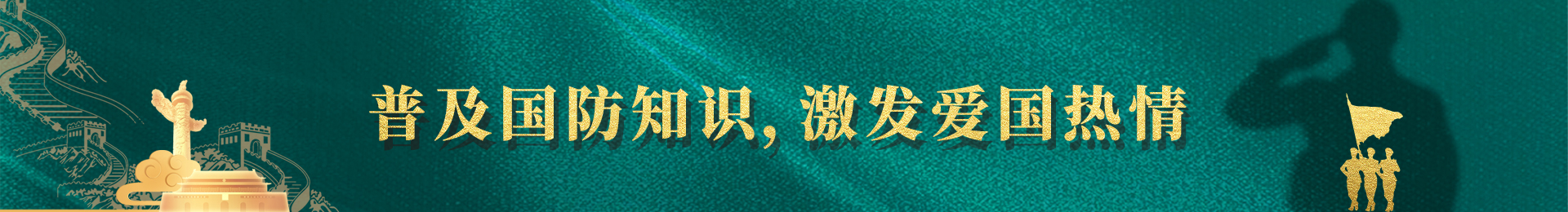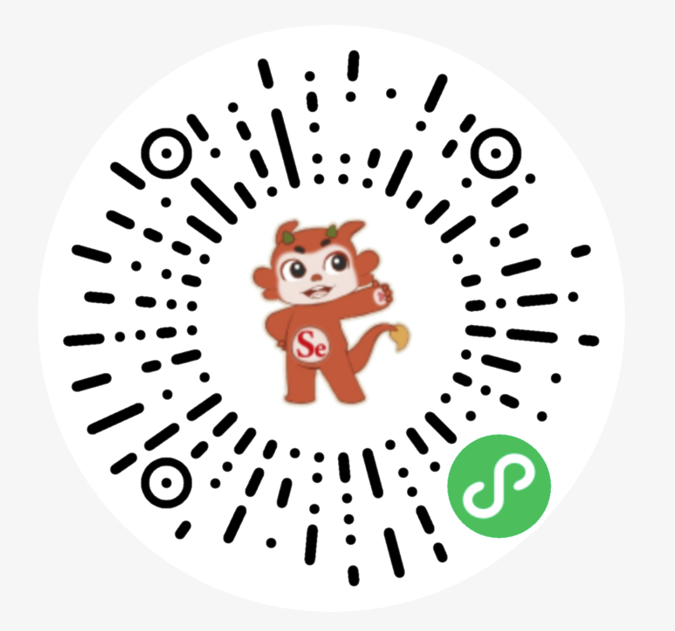协会地址:苏州市虎丘路88号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总装备部某基地副政治委员 侯力军
林俊德同志是“两弹一星”伟业的重要开拓者,是我国自己培养的核科学家。为铸就国家和平盾牌、挺立中华民族脊梁,他拼搏奋斗了一生,默默奉献了一生,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的感人事迹和献身精神,浓缩为一句话就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上世纪50年代,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党中央、毛主席作出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一批批海外学者、专家教授、高校学子,响应祖国号召,从四面八方奔赴核试验基地。林俊德就是第一批选调到基地的优秀大学生。当得知自己将从事核试验时,他说,报答党和人民的时机到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林俊德研制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在第一时间就准确地测到了核爆炸的冲击波数据。当周总理问,这次爆炸是不是核爆?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根据林俊德提供的数据,坚定地向总理报告,测量数据证明是核爆。那一刻,林俊德无比兴奋。他说:“想不到自己干的事情这么重要,周总理都这么重视和认可,一下子就感到了肩上的责任。”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是“两弹一星”创业者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林俊德身上,这一精神所产生的巨大力量,超越了现实成为信仰,跨越了时代成为永恒,支撑着他一生为国家尽心、为事业尽力。
当年,试验场选在荒漠戈壁,搞核试验一辈子隐姓埋名、只干不说。直到今天,林俊德的许多成果还不能公开,甚至一度影响他评选院士。但他和他们那一代创业者一样,留名只留集体名、计利只计国家利,只要国家强大了,就是他们最大的光荣。
特殊年代,林俊德默默奉献;时代变了,他依然默默坚守。身为院士,他亲力亲为不要助手;身为将军,他艰苦朴素不图享受。汶川地震后他悄悄捐了3万元,他默默资助着10多名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去世后,他的老伴黄建琴大姐又把组织上给的10万元慰问金,作为林俊德的最后一次党费全部上交。
住院时,他特意准备了一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着需要处理的事情:完善技术方案,审改学生论文,家人留言等11件事。去世后,我们打开他的小本子,其它10项事情他都一一安排好了,唯独“家人留言”这项还是空白,一个字也没有留下。弥留之际,他留给组织的一句话就是:“把我埋在马兰。”林院士身上插着4根管子、头戴氧气罩、手握鼠标工作的场景,如同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用身体堵枪眼的黄继光,他用一个战士冲锋的姿态跨越了生死之界,他跨越的是如此壮美、壮烈!
在马兰戈壁滩上,生长着一种名叫胡杨的树木,它死后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朽。人们说,林俊德就是一棵扎根大漠戈壁的胡杨树,就是一名永垂不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发狂”工作创造“中国速度”
■中国工程院院士、总装备部某基地研究员 邱爱慈
我和林俊德院士是同事,我们都是从“两弹一星”那个火热年代走过来的,同样的理想抱负,同样的事业平台,同样的成长经历,让我对他有着更深的了解。
林院士常说:“一个人的成功,一靠机遇,二靠‘发狂’。”他说的机遇,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决策研制“两弹一星”;他说的“发狂”,就是从事“两弹一星”时的那么一种干劲,那么一种热情,那么一种奋斗精神。
当时,我们在核试验场区住的是帐篷、地窖,喝的是又苦又涩的水。生活上的苦大家觉得不算啥、好克服,最难、最考验人的还是尽快攻克科研中的难题,圆满完成国家任务。核试验是事关国家和民族安危的高尖端技术,从来都是要不来、买不来的,面对国外的封锁和压制,我们都憋着一口气,把原子弹当作“争气弹”,决心白手起家,卧薪尝胆,依靠自己的力量,一定要把它搞出来。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大学毕业没几年的林俊德受命研制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仪器。研制这种仪器最难的是动力问题。国外的机测仪器一般是用小型稳速电机作动力,但这项技术当时我国还没有掌握。怎么办?林俊德整天苦思冥想,连吃饭、走路都在思考,有一天,受街上电报大楼钟声的启发,林俊德产生了灵感——决定用钟表发条作动力,设计钟表式压力自记仪。接下来需要解决压力自记仪的压力标定问题,在没有正规实验室的条件下,他们因陋就简,在铁铺里焊了个贮气罐,用自行车打气筒往里打气来替代。经过一年半艰辛探索,他们研制出能在核爆炸电磁脉冲等恶劣环境下可靠工作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在首次核试验中试用成功,测到了准确完整数据。
1966年的冬天,我国首次氢弹试验不久将要进行。这次试验方式由塔爆改为飞机空投,需要在高空对冲击波进行测量,必须尽快解决自记仪高空防冻、高空定点、落地防震等一系列难题。为了更真实地模拟仪器使用环境,他们又爬到海拔近3000米的山顶。冬天的山顶空气稀薄,冰封雪冻,寒风刺骨,他们在零下20多度的山顶上呆了整整一夜,手冻僵了,脚冻麻了,连胡子和眉毛上都结了一层霜……回顾那段岁月,正是有一大批像林院士这样“发狂”工作的科研人员,我国不但成功炸响了原子弹,而且用比其他核大国都短的时间炸响了氢弹,创造了让国人振奋、令世界震惊的“中国速度”。
一个人“发狂”工作,一阵子容易,一辈子很难啊。林院士用一生的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在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今天,我们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应该像林院士那样,胸怀祖国,珍惜机遇,奋发工作。有了这种精神,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就没有干不好的事。
陪伴老林一辈子我很幸福
■林俊德院士妻子 黄建琴
我和老林既是夫妻,又是同事,都是核试验科技队伍中的一员。我们在戈壁滩上相识相知,一起工作生活了45年。
我是1963年从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来基地的,那时我国正准备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千军万马会战在戈壁滩上。当年我们一起去的有40多个女同志,住在5顶帐篷里,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把它取名叫木兰村。我和老林是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认识的,又是在第一颗氢弹试验那一年结婚的。
老林对工作的投入近乎痴迷,为了核试验什么都不顾。记得女儿快出生时,老林正忙于试验任务,加之当时基地物资供应欠缺,我和我们那一代许多女同志一样,怀孕后都是回老家生孩子。我从马兰坐长途汽车,颠簸了10多个小时到吐鲁番火车站,由于快要过春节了,买不上卧铺票,坐着硬座熬了4天4夜到南京,又坐了10多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才回到苏北老家。女儿满月时,老林才来接我,考虑到当时工作忙,加上戈壁滩生活条件艰苦,实在没办法抚养,他悄悄地和我商量:“把孩子托付给大嫂吧。”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大嫂有6个孩子,最小的才4岁,生活过得艰难。当我含着眼泪说出想法时,大嫂为难地说:“不是我不愿意带,是孩子太多,实在怕照顾不过来。”我们狠了狠心,对大嫂说:“孩子养不活,我们不怨你。”大嫂这才将我女儿接到怀里。
老林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一直觉得愧对孩子。一次他对女儿说:“你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爸爸妈妈没有养育的经验,你就当是我们的试验品吧。”老林感情不轻易外露,可说这话时,我看见他眼里含满了泪水。其实老林是非常疼爱孩子的。他知道女儿爱吃新疆烤馕,每次出差路过乌鲁木齐,总要亲自排队给女儿买几个;儿子从10岁离开我们去外地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老林给儿子写了100多封信,这些信儿子至今还珍藏着。
在北京,他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尽管北京的医疗条件很好,但老林不肯在北京继续住院,反复对我说:“建琴呀,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得赶紧回单位处理工作上的事。”为了他工作方便,5月23日,我陪老林转到西安唐都医院,刚入院他就催着我回家把笔记本电脑给他拿来。在随后的8天里,看着他用颤抖的手批改学生的论文,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还要整理电脑文件,我的心像刀割一样。
老林住院的60多天,是我们夫妻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老林对我说,“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从没说过‘我爱你’,但实际上我都努力做了。”我们虽然缺少点浪漫,但我觉得我们过得很和睦、很充实。
老林住院期间经常说:“我75岁了,这辈子干了核试验这件事,我很满意。”这是老林的心里话,也是我们那代人的共同心声。把一生献给国防科技事业,我们觉得很光荣;陪伴老林一辈子,我觉得很幸福。
恩师永远引领我们前行
■总装备部某基地技术部总工程师 钟方华
我是林院士的学生。在我办公室书柜的正中间,摆着一个钟表式压力自记仪,每当看到它,老师的身影就浮现在眼前。老师的一生就像他研制的压力自记仪那样,虽然简单却很精准,尽管朴实却很高效,看似平凡却蕴含智慧,始终引领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成长。
一次课题攻关,老师就带着我们在实验区的空地上,挖了个2米多深的土坑进行探索性实验。土坑里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如冰窖,遇到下雨积水可以养鱼,可老师全然不顾,坚持和我们一起爬上爬下做实验,一干就是几年。那段时间,同事们背后悄悄地称老师为“民工院士”。
讲实效、讲创造性,对国家负责,是老师科研创新的一贯思想。他最善于用简便实用的方法解决复杂技术问题,发明压力自记仪,就是用简单的钟表发条代替结构复杂的电机;他用两根普通的铜丝,巧妙解决了声靶检测系统的传感器标定问题;就连戈壁滩上的沙子,也被他“点石成金”,用作大型实验装备的一种特殊材料。这些发明创造看似简单,却显示了老师厚实的功底。
老师临终前,用102秒给我们留下了163个字的遗言,他讲:“马兰精神很重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希望大家继承马兰精神……”这是老师的生命嘱托,我们每个学生都把它珍藏在手机里,每次看到、听到这段话,老师的音容笑貌就历历在目。
在老师电脑里,他为每名学生都建有一个文件夹,里面详细记录着每个人的性格特点、技术专长、培养计划。今年老师生病住院后,他特意让师弟把文件夹拷走。那时,大家才惊讶地发现,从跟老师的第一天起,我们每一步成长,老师都悉心为我们规划着、记录着。病重期间,他也时刻牵挂着学生。张博士的毕业论文,是老师在北京住院期间修改的。去世前6天,他还强忍病痛花了两天时间,断断续续审改了唐博士8万多字的毕业论文。
老师住院后,学生都想去看他,全被他拒绝了。他在电话里说,今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你们都要坚强、要努力,我觉得老师的话,就像是一位父亲对孩子独自出门时的深情嘱托。5月23日,我出差路过西安给师母打电话,想去医院看看老师,他却让师母转告我,不急,回去好好工作吧,以后有的是机会。我很不情愿,又不好违背老师,谁知这竟成了我终生的遗憾。5月31日,对许多人来说,是个平常的日子,对我却是那样的刻骨铭心。当我赶到医院时,老师已昏迷不醒,我拉着老师的手贴在脸上,泪流满面地说:“老师,你像父亲那样摸摸我的头,好吗?”老师的手好像轻微动了一下,我想,他一定是听懂了学生的呼唤。
敬爱的恩师走了,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老师用生命之火给了我们温暖和爱,用精神品格教会了我们做人做事,我们接过老师手中的接力棒,为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微薄力量。
最后8天壮美的生命绝唱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惠宾科护士长 安丽君
临床一线工作了20年,护理过许许多多身患绝症的病人,与林院士接触的短短8天,却让我永生难忘。
5月23日下午5时,我在病房第一次见到林院士。他身形消瘦、面容憔悴,言谈举止却淡定从容,丝毫看不出身患重病。翻看他的病历后,才得知他患的是胆管癌,已到晚期。多年临床经验告诉我,生命留给老人的时间不多了。
5月24日上午9时,我们与他商讨治疗方案。一听说要做手术和化疗,他当即回绝:“我之所以没有在北京做,就是担心术后影响工作。”我们实言相告:如果手术,可能会延长一些生命;不手术癌细胞会很快扩散。他却十分平静:“如果不能工作,多活几天又有什么意义?”听了这,我倍受震撼:是什么原因让他面对生死如此从容,是什么信念支撑他为了工作宁愿放弃手术治疗?
5月26日下午3时20分,林院士病情突然恶化,出现消化道大面积出血,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经过一天的紧张救治,病情稍好转,林院士便急切提出:“在这里没法工作,请把我转回普通病房”。考虑到他身体状况,我们不同意。他说:“这样呆着,比死了还难受,我宁要有质量的一天,也不要没有质量的十天。”
5月30日下午4时45分,因为肠梗阻林院士肚皮胀得发亮,心率快得接近正常人的两倍。这样的状态,即便是躺着什么都不干,都是一种煎熬。林院士身上插满了胃管、引流管、输液管,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科室一名“80后”护士哽咽着说:“林爷爷躺着是病人,站起来是战士。”
在我眼中,林院士不是一名普通的病人,他是一名转移了战场、战斗在病房的战士。虽然我不知道他拼命也要做完的工作具体是什么,但我知道那一定很重要,比他的生命更重要。
5月31日,林院士住院后的第8天,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似乎感到死神的脚步已经迫近,从7时到9时,他先后9次发出强烈工作请求。老伴说不通他,女儿劝不住他,我们医护人员拗不过他……
10时54分,他颤抖的手已握不住鼠标,视力渐渐模糊。劝他休息,他说“我不能躺下,躺下就起不来了”。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林院士越来越虚弱,但他依然在坚持、在冲刺……
11时09分,我们极力劝他休息,他最后一次查看了电脑里的文件,艰难地说:“好吧,谢谢!”他累了,躺下了,这一躺就再也没有起来。20时15分,那波动的生命曲线永远消失了。那一刻,从医30多年的科主任张利华,跪倒在病床前失声痛哭:“林院士,您是我最敬仰的病人!”我和同事们眼含泪水为他擦洗身体、整理遗容……
短短8天,林院士走了。这8天,让我亲眼目睹了一名共和国院士的鞠躬尽瘁。他壮美的生命绝唱,将激励我们在平凡岗位上勤奋工作、报效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