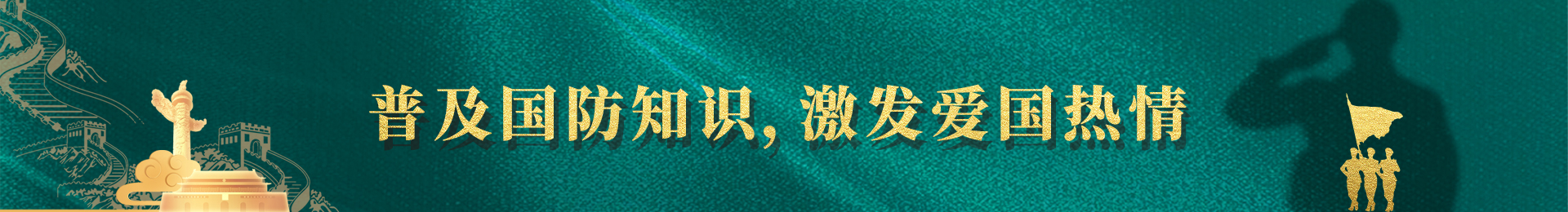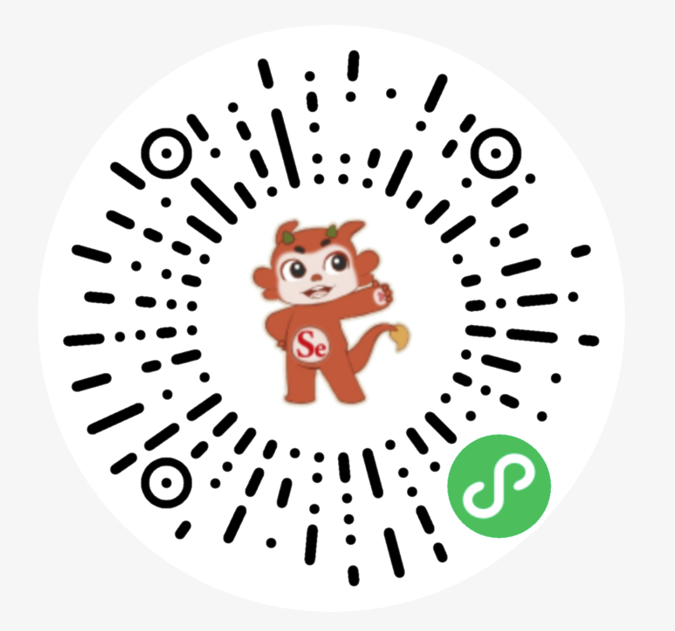协会地址:苏州市虎丘路88号

李曙光近影。李 波摄
李曙光又有10多天没走出实验室了。
9月的山城重庆高温渐退,可在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里,研究员李曙光仍忙得满头大汗。作为全军重大科研项目“人体防护工程”的首席科学家,他全身心投入其中。
“这个项目完成后,会让我军官兵穿上‘无形盔甲’,这在未来战争中将保护多少生命啊!”谈及正在进行的研究,他满脸兴奋。
李曙光,人称“野战救护铸盾人”。在实现强军目标的征途中,他呕心沥血,一次又一次为战士生命防护带来曙光。
他研制的系列扫雷防护装具被联合国列为维和装备,研制的两栖装甲救护车填补我军空白——
“战场生死较量,防护必须一流”
在有“死亡地带”之称的黎以边境临时停火线上,中国维和工兵创造了清排万余枚地雷无一伤亡的奇迹。他们身上穿着的,就是由李曙光研制的全套扫雷防护装具——防雷服、防雷鞋、防雷头盔面罩以及防雷护手护臂。
目前,这套装具已达到世界最高防护级别,被联合国指定为维和装备,在26个国家的扫雷维和部队中广泛使用。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向世界郑重宣布:将在云南、广西边境进行大扫雷。
扫雷部队指挥部向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求援,请求解决排雷防护设备问题。这一重担,最终压在了李曙光肩上。
一双小小的防雷鞋,涉及生物医学、力学、材料学、结构学等多门学科。李曙光扎进实验室,昼夜鏖战。
28天后,他带着研制出的防雷鞋赴雷场做模拟试验,试验地雷TNT当量为50克。一声爆炸后,模拟人腿的肢体安然无恙!扫雷指挥长一把抱住李曙光:“老李,我们终于有了能完全防护地雷的鞋子!”
李曙光没有止步,目光又转向TNT当量210克的地雷。这是世界上威力最大的防步兵地雷,爆炸致残率为100%,致死率达到60%以上。
经过反复试验和改进,李曙光确定了阻挡、分离、偏移爆轰冲击波以及衰减、缓冲爆震波的防护思路,在半年后研制出新式防雷鞋,成功防住这个当量的地雷。
“战场生死较量,防护必须一流!”李曙光追逐强军梦的脚步片刻不停。2001年夏,一场三军协同演习在某海域激战正酣。两辆涂红十字的两栖装甲救护车踏海破浪,泛水20海里后紧随部队抢滩登陆,进行伴随救护和滩头定点救护。
这种首次出现在我军作战序列中的装甲救护车,是李曙光带领团队攻关的成果。现代战争破坏力极强,肩扛手抬救治伤员的模式已不能适应未来作战需要。李曙光申报了两栖装甲救护车研制课题,打造伴随战士冲锋的救护装备。
把装甲车改造成救护车涉及几十个学科、上万个元器件,让诊治救护设备与其他功能设备兼容运行,还要保证伤员不受到新创伤,难度可想而知。李曙光带领课题组把行军床搬到军工厂车间昼夜试验,两个月后样车成功下线。经测试,各项性能均达到国际同型装备先进水平。
随后,他们成功研制出轮式、履带系列装甲救护车,使高原、高寒、湿热、沙漠、山岳丛林等多种环境下的伴随救护有了新平台。
记者在装甲救护车内看到,里面配有监护仪、呼吸机、输液泵、制氧机、急救药品器械,以及战伤急救辅助诊断系统、缓冲减震的担架床和伤员座椅等,能完成紧急救治、生命支持和快速护送。目前,装甲救护车已列装我军多支作战部队。
他被称为“科研铁人”,难题压不倒,危险吓不住,身上始终奔腾着攻坚克难的热血——
“怕苦怕死,还搞什么战场防护”
“我们都有强军梦,但梦想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实现的,怕苦怕死,还搞什么战场防护?”李曙光常对身边的年轻同志说。
李曙光是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出生的,老伴调侃他:一出生就是劳动的命。多年来,他的日程表中没有节假日。从实验室到家的路只需步行5分钟,他却经常扎在实验室,就连春节也大都在基层部队和工厂度过。常年加班熬夜让他常掉头发,同事们看了心疼,他却说:“掉点头发算什么,只要没掉脑袋,就继续干下去。”
那年夏天,李曙光带领团队在兵工厂搞装备研制,身上衣服全被汗水洇湿,连三班倒的工人都累得说:“这样干下去,连铁人都得化啊!”第三军医大学领导带队去调研,到现场看了一圈都没能把他认出来:满身油污,油味刺鼻,李曙光从此便有了“科研铁人”的称号。
一次,李曙光患重感冒发烧,但坚持按既定日程到东北寒区部队调研试验。一台救护装备在试验中“趴窝”,李曙光为找到故障原因,脱下手套钻到装备底盘下忙碌了一个多小时,结果双手被冻伤。同事说:“老李,你对装备比对自己还好,真是不要命了!”
说起不要命,李曙光的故事可真不少。扫雷防护装具装备扫雷部队后,它的可靠性究竟如何?李曙光当场穿上防雷鞋和防雷服:“今天的雷场我先上!”
2011年夏,李曙光带领科研小组在某海域开展两栖装甲救护车性能试验。突然间风起云涌,大雨倾盆。然而,这正是测试装甲救护车恶劣天候下性能的好机会。李曙光穿上救生衣爬到装甲救护车顶上,从容下海。
大海中的装甲救护车就像一片树叶,有个巨浪打来差点将它淹没。李曙光身体剧烈摇晃,他死死地拽着救生绳,亲身体验车辆性能。为获取海水浸泡伤救治的准确数据,他不穿潜水服扎到海里进行试验。
他科研的“准星”始终是“战时管用、部队急需、官兵期盼”——
“眼睛不盯着战场,还穿军装做什么”
老伴毕丽与李曙光相伴几十年,只见他哭过一回。那是他从边境作战前线调研回来,含着泪对她说:“你不知道战士们在前线有多苦、多累、多险,我是搞科研的,眼睛不盯着战场,还穿军装做什么?!”
采访李曙光,我们又被他的笑容感染。谈起自己的科研成果时,他笑得十分欣慰:所承担的课题100%来自部队,成果100%运用到部队。
“战时管用、部队急需、官兵期盼”,是李曙光不变的科研方向。他每年用三分之一多的时间深入部队搞调研,先后为军委总部提交论证、方案30余项,为我军综合保障装备发展的顶层设计提供了可靠依据。仅在大型卫生装备研制过程中,他就奔赴20多支部队和工厂企业进行调查论证,总行程超过百万公里。
李曙光当过战士、宣传员和教员,最初学工科后来改学医学。调到第三军医大学接触医学这个全新领域时,李曙光已过而立之年。他一边和比自己小10多岁的学员一起学习医学知识,一边协助专家教授做试验。3年后,他获得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硕士学位,为野战防护科研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他在创伤弹道学领域,一举摘取了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军“九五”重大科技成果奖等多项桂冠。
李曙光的目光,始终紧盯世界军事斗争的前沿。着眼现代战创伤的新变化,他提出并推动建成我国首个“武器杀伤生物效应评估中心”,使我军有了为火力毁伤、战伤救治等理论研究提供科学鉴定的权威机构。
李曙光在军事科研的征途上,心里装着战士安危,此生只为铸盾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