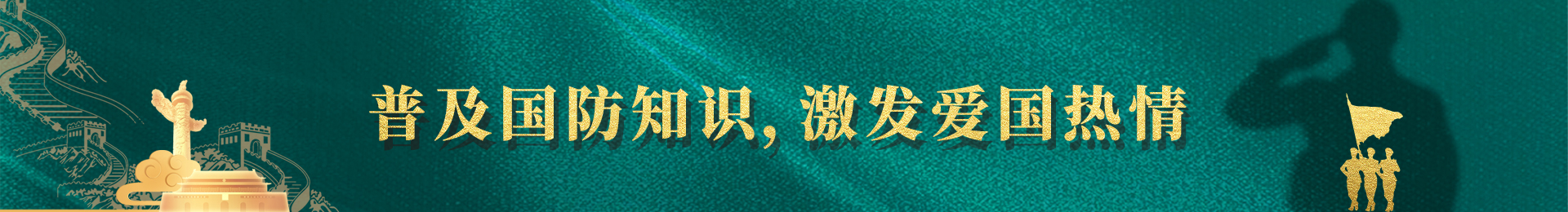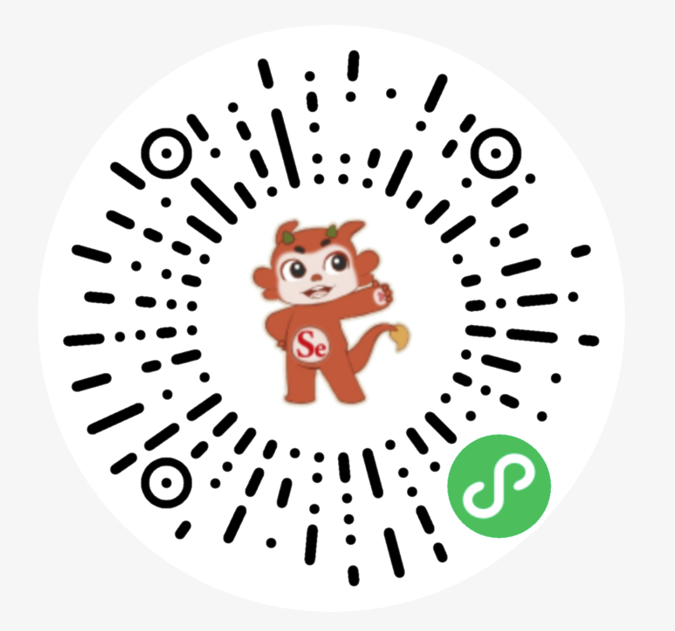协会地址:苏州市虎丘路88号

贾元友
信息化时代来了,信息化战争来了!作为一个士兵,出路只有一条——
向着信息化高地冲锋
北京军区某机步团战士 贾元友
我是一个成长在和平年代的普通士兵,既没有经历过枪林弹雨,也没有做出过英雄壮举,是部队这所大学校哺育我成长成才,是军队的转型发展让我实现了人生价值。
我出生在山东农村,父亲当年是内蒙古边防的一名骑兵。30年来,他策马冲锋的照片,一直摆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让我从小就对军营产生了向往。
记得第一次钻进新型坦克,面对密密麻麻的开关按钮和液晶显示屏,我的两只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手心里全是汗。就在那年底,一批昔日的训练尖子因为缺乏信息化知识,适应不了新装备的要求,选择了退伍返乡。最让我震惊的是,我的偶像、全团第一射手,也因跟不上训练进度,没能晋升更高一级士官。看着他黯然离去的身影,我猛然发现,在部队转型发展中,不懂信息化,就要被无情地淘汰!
说实话,如果我不爱坦克,淘汰吓不住我。可我已经融入了这绿色的方阵,3天听不着马达响,闻不着柴油味,就像丢了魂,心里空落落的。我曾私下问连长:“有没有不换新装备的部队?我想去那儿。”连长眼睛一瞪,说:“那你就去博物馆,那里永远都是老装备。”
没过多久,伊拉克战争爆发了。电视上的战场直播,既让我大开眼界,又让我心灵震撼。全新的作战手段,广阔的作战空间,瞬息万变的战场信息环境在告诉我:信息化时代来了,信息化战争来了!作为一个士兵,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直面挑战,向信息化高地发起冲锋!
转型的过程犹如浴火重生。第一次拿到新装备的操作教材,我翻了两页就再也看不下去了,那些字母和公式我几乎一个也不认识。如果说向信息化高地进军,别人起步就是百米冲刺,而我却是在匍匐和攀爬中前行。初中文化的底子,经过打工几年的淡忘,早已所剩无几。为了弄懂一个公式,我向排里的新兵请教;为了记住那些操作流程,我兜里装满了自制卡片;为了掌握射击要领,我钻进坦克就忘了出来。坚持不懈的勤学苦练,我渐渐尝到了甜头:接受理解能力增强了,工作效率提高了,过去认为的“天书”也渐渐看懂了。我越学越有劲,越学越有兴趣,渐渐把学习变成了快乐的事、幸福的事,变成了一种习惯和生活状态。
作为陆军转型探路的先行部队,我们前无古人,但后有来者。作为新装备的第一代操作者,开好每一次车,打好每一发弹,攻克每一道难关,既是本部队新装备形成战斗力的迫切需要,更是为后续部队积累经验的基本要求。无论是编写新装备操作使用教材,修正高原火炮射击偏差,还是解决自动装弹机卡弹等问题,我都认为自己责无旁贷。我想,作为一个兵,平时遇到问题自己解决不了,可能会有人帮助你,但上了战场,敌人绝对不会给我们等靠的机会。
我一次又一次攻克前进路上的难关,一次又一次刷新自己的纪录,一次又一次淘汰过去的自己。每当遇到看似无法逾越的困难时,我都对自己说,贾元友,我要向你挑战!
我军一位知名射击专家问我,如果给你4发穿甲弹,能不能在规定距离上,打到一个脸盆大小的区域内?当时,我想都没想,说:“不可能!”没想到他却说:“我就能。”他的自信既让我佩服又让我羞愧。我虚心向他求教,经过上千小时的训练,学习掌握了他总结的“肌肉记忆法”。2010年6月25日,我在军区比武训练期间,连续打出的4发穿甲弹,全部命中靶心,打出了做梦都在追求的理想精度。宣布成绩的那一刻,我兴奋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10几年来,我先后操作过两代三型坦克,在与装备的磨合中我渐渐领悟到:信息化时代,无论装备多先进,人依然是战斗力生成的重要因素。作为一名信息化士兵,就是要竭力做到人脑与电脑相通,神经与链路相连,肢体与车体相融。我相信,只要勇于挑战,不断超越,我们就一定能在未来战场上用事实证明:中国不仅拥有世界一流的装备,更有世界一流的士兵!
今年是我入伍的第14个年头,一路走来,家里人理解我、支持我,使我能够心无旁骛地在部队尽自己的职责。2006年5月,妻子已怀孕6个多月,由于部队即将野外驻训,我只请假回家陪了她两天。走的时候,她硬是挺着肚子,送我去车站。一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快上汽车时,她突然抓着我的手说:“给孩子取个名字吧,等你下次回来,都不知道他有多大了。”车子开动了,她挺着肚子努力地向前追了几步,不停地向我挥动着双手。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夺眶而出。
最让我难忘的是,今年5月23日,在军区第十次党代会上,我作为基层代表,受到了胡主席的亲切接见。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热情鼓励,让我感到无比温暖。我深知,这既是对投身信息化建设全体官兵的至高褒奖,更寄托了党和人民对新一代官兵的殷切期望。我由衷感到:一个基层士兵,能够在履行使命中实现人生的价值,是多么自豪、多么光荣!成绩和荣誉属于过去,我一定牢记使命,永不停步,继续向信息化高地奋勇冲锋!

许为飞
我坚信,拥有这样的士兵,我们一定能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士兵楷模 转型尖兵
北京军区某机步团政治委员 许为飞
我和贾元友来自同一支英雄的部队。为陆军信息化转型探路的光荣使命,催生出一大批信息化精兵,贾元友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今年7月,我师远赴塞外参加实兵对抗演习,贾元友所在的坦克冲击在右翼突击群最前沿。突然间,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激光测距仪无法获取准确数据,贾元友通过蓝方坦克在热成像仪中呈现的比例,测算出射击距离。“激光测距改为人工装定,锁定目标开火。”蓝方阵地前沿实体坦克目标被全部摧毁。
看着今天的贾元友,谁又能想到,入伍时他是一个连电脑都没有用过的初中生?
2001年,我军某新型主战坦克在我团首先列装。前所未有的本领恐慌,震撼着全团官兵。
对贾元友来说,转型就是一座山!他拉开豁出命的架势,每天多学1小时,10几年来,至少挤出了5000多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先后修完中专、大专、本科学业,取得军事学学士学位。在全团战士中,他第一个通过国家计算机二级考试,第一个建起新型主战坦克资料数据库,考取坦克通信、驾驶、射击三大专业特级证书。
2011年,我师师长到国外考察信息化建设情况,回国第二天,贾元友就找到他,软磨硬泡要来考察笔记。有一次,贾元友到某陆航团作报告,追着团领导请教直升机的性能战法,该团团长开玩笑地说:“你给我们作了20分钟的报告,我们却回答了你两个小时的问题。”
凭着这股执著与坚守,贾元友编写出第一本新型坦克操作使用教材,参加了训练考核大纲编修任务。谈起自己的成才经历,贾元友总是说:“我们不怕慢于他人的初速度,但一定要有高于他人的加速度!”
2006年夏天,我团挺进内蒙古草原,组织新装备首次实弹考核。然而,第一次实弹射击,合格率竟然没到50%,许多老炮手当场就哭了。
贾元友泡在坦克上,一干就是7天,绘制出了不同时段火炮射击修正曲线图,使命中率大幅提升。正式考核那天,总部首长随机点将,31发炮弹命中30发。当得知是贾元友解决了“打不准”的问题后,一位专家竖起大拇指说:“这支部队了不得,小兵也能挑大梁!”
当晚,团里给攻关小组摆了庆功宴。当大家在篝火旁庆祝时,我的手机响了,贾元友的家人通过团总机找到了我。刚听了两句,我就兴奋地吼了起来:“贾元友,你媳妇生了,生了个儿子!”贾元友接过电话,传来妻子虚弱的声音。因为难产,他媳妇差点丢了命。贾元友拿着手机,反复说着一句话:“对不起,对不起……”他深爱着自己的亲人,但他把国家的安宁看得更高、更重!
14年来,贾元友先后荣立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被评为全军爱军精武标兵、全军学习成才先进个人和全军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在他的带动感召下,我团掀起了“学信息化本领、当信息化尖兵”的热潮,连续3年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团”。
我坚信,拥有这样的士兵,我们一定能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罗振国
一个士兵能走多远,取决于他能看多远,一个士兵的舞台有多大,取决于他心胸有多宽——
我的班长我的星
北京军区某机步团战士 罗振国
我是贾班长一手带出来的兵,在同一辆战车上并肩战斗了6年。我亲眼目睹了他一次次超越自我的艰辛,也一次次被他的坚韧执著所折服。我崇拜过歌星,迷恋过球星,现在,贾班长才是我心中最亮的星。
到部队的第一天,来接我的就是贾班长。他高个子、黑脸庞、大嗓门,点了我的名字,拎起行李就走,我在后面一路小跑才跟上。
凭直觉,我感到这个班长很厉害。果不其然,贾班长的严格要求让我们难以招架。更要命的是他眼里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一次,团里组织队列会操,我们班名列第二。当我们得意洋洋等待表扬时,他反而把我们拉回了训练场,冲我们就吼:战场无亚军,第二就意味着失败!接着,又给我们训练补课。他的种种苛刻要求,真让我们有些受不了。
生气归生气,但我们慢慢发现贾班长确实有本事。5公里越野,他把第二名甩出100多米;掰手腕,他打遍全营无敌手;打篮球、踢足球,只要他在场,我们总能赢。特别是我们第一堂战术训练课,贾班长为我们做匍匐示范,他“飞”一般向前滑出两三米,石子划破军装,也划破了胳膊和手掌,但他全然不顾。开始,我们都有点害怕,但在贾班长的带领下,我们都勇敢地向前扑去。
彻底让我服气的,是那次演习。我和贾班长同驾一辆战车,就在我们准备射击时,意外突然发生了,药筒卡在了炮膛。只见贾班长用手猛地将炮弹推进炮膛。随着“轰”的一声炮响,靶标被摧毁。贾班长向我伸出两根手指,作出胜利的“V”字,我看到他的手鲜血直流。
演习在有惊无险中结束,可那发炮弹还像鱼刺一样卡在贾班长的喉咙里。看他的倔劲又上来了,我劝他:“班长,装备的问题有专家,我们就别操这个心了。”贾班长脸一沉:“这也等专家,那也等专家,上了战场我们等谁去?”
当时正值盛夏,坦克装甲上都能摊鸡蛋饼,舱里气温高达50多摄氏度,贾班长一扎进去就是一两个小时,每次出来都像蒸了桑拿一样。一周后,他摸索出了“排除卡弹五步法”,在全团推广后,卡弹率降低了80%。
今年7月,贾班长在一次实兵对抗演习中,更是打出了威风。以前,我们都是打土堆靶、木板靶、纱布靶,这一次头一回打实体坦克。面对实打实的真家伙,贾班长一下子来了劲头。他对我们说,“敌人”的炮口正瞄准你,你不摧毁它,它就消灭你!在2000多米的距离上,贾班长的炮弹像长了眼睛,准确命中,击爆油箱,引起了熊熊大火!到了现场,贾班长在依然发烫的坦克上钻进钻出,欣喜若狂!他激动地说,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新装备的威力!
跟着贾班长这几年,我深深悟出一个道理:一个士兵能走多远,取决于他能看多远,一个士兵的舞台有多大,取决于他心胸有多宽。我为有这样的好班长而庆幸!当兵就要当贾班长这样的兵!

王东军
有这样天天想着打仗的战士,我们有什么难关不能攻克,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战胜——
我眼中的“士官教授”
装甲兵工程学院兵器工程系副教授 王东军
2011年,根据总部要求,学院派我到贾元友所在团任副团长,帮助部队抓好新装备训练。
有一天,一个憨厚壮实的战士敲开了我的门:“王教授,我叫贾元友,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您看方便吗?”交谈中,我惊讶地发现,贾元友不但对坦克射击专业非常精通,而且对作战运用研究得很深,更深刻地感受到他那强烈的求知渴望。
一天晚上,贾元友带着他的问题又来了。“王教授,新装备为什么多了个自动装弹机备用控制盒?应该怎么用?老装备为什么没有?”我不敢轻易下结论,只好拿起电话向朋友、向兵工厂的专家求助,最后也没找到答案。
考虑到当时很忙,我对他说:“这是个小问题,先放一放吧。”贾元友一听急了:“今天是小问题,明天上了战场可就是大问题!”我只好放下手头工作,带着他研究了两天,终于找到了答案。看着他欢天喜地地走了,我如释重负,又感慨万千:有这样天天想着打仗的战士,我们有什么难关不能攻克,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战胜!
2011年初,团里派我们到厂家接新装备。贾元友就找到我,说:“现在新装备只有说明书,回到团里大家没法练。”我拿出一本某型步战车武器使用教材给他看,贾元友翻了半天舍不得放下,连声说:“我们就缺一本这样的书。”我将了他一军:“不行你也编一本试试?”贾元友思索片刻,说:“试试就试试!”
贾元友说干就干。实车操作,他车上车下、车里车外,忙个不停;工厂技术人员讲完课,常常被他堵住,没有一个能顺利“脱身”。6万多字的新型坦克操作使用教材出来了,贾元友像大病了一场。团长看到书稿后,连声赞叹:“好,太好了!有了这本教材,新装备一到,部队就能展开训练。”
后来,在总参召开的全军新装备模拟训练器材鉴定会上,我把这本教材推荐给与会专家。鉴定过程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这本教材,当成评价新型坦克射击模拟器的主要依据。会后,许多同行祝贺我:“王教授,恭喜你又出了一本大作。”我自豪地告诉他们:“这不是我编的,是贾元友!我代职部队的一名士官!”
新装备接回后,面对部队官兵文化起点不同,素质参差不齐,如何集中组训,我心里没底。一天,我在坦克二营,发现贾元友把全营30多名炮手分成四组,第一组学基础理论,第二组基础练习,第三组实装操作,第四组实装考核。这就是贾元友创造的“岛链式晋级训练法”。他告诉我:“一个组就是一个岛,一个岛比一个岛难,就像闯关游戏,过了这一关才能到下一关,解决了少数人练、多数人看的问题。”一个战士有这样的任教水平和创新精神,我发自内心地感叹:贾元友,“士官教授”,真是名不虚传!
这些年,我到过全军很多单位,也接触了许多优秀士兵,贾元友是尖子中的尖子,精兵中的精兵。他的专业知识和信息素养,远远超出了普通士兵;他的教学能力和研究层次,值得我们专家教授学习借鉴。

文 静
准备好了吗?士兵兄弟们,当那一天真的来临——
青春,为使命绽放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 文 静
作为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我一直向往军营,崇拜那些为国家和人民浴血奋战、无私奉献的军人。采访贾元友的事迹,使我有机会再一次走进军营,走近新时期共和国年轻的士兵。
我的采访从训练场开始。贾元友身躯高大,但登上坦克、进入战位的动作却极其矫健,一个腾跃,就到位了。而我小心翼翼,却不时被铁板碰撞。我问贾元友:“你开坦克,没少碰着吧?”贾元友说:“是啊,但真正的碰撞却不是身体与钢铁,而是新与旧,从感情到能力,到观念,一开始就碰得头破血流。”
我问贾元友:“那又是什么让你走到今天?”贾元友回答:坦克。这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又问:“可你说过‘我爱坦克,坦克却不爱我’?”贾元友沉默了。在我的追问下,我了解到,坦克兵的理想身高是1米65,而他1米77,在坦克舱内连腰背都挺不直,与坦克碰撞十几年,他多次经历破皮断骨之痛。但我要探寻的是,在大变革年代,他靠初中文化的底子,在高学历军人云集的军营脱颖而出,在精神上、心理上到底经历了哪些坎坎坷坷?
那年,刚刚列装的新型坦克再一次强烈地震撼了贾元友。战斗室里,贾元友看不到熟悉的摇柄和拉杆,而是陌生的车载计算机和密密麻麻的按钮,他彻底蒙了。
焦虑、恐慌、惧怕,转型期的各种磨练,他都在体验。不要说转型时代的万水千山都在阻击他,仅小小的键盘关就何其难闯。他请教新兵怎么练的,人家说从小妈妈教手风琴,键盘一摸就会了。贾元友长久地徘徊辗转,最后躲到营院偏僻处泪如雨下。
风雨过后是彩虹。贾元友与坦克兄弟风雨同舟,心心相印。他先后以极高的标准获得了坦克通信、射击、驾驶三大专业的特级资格,连续创造师、集团军直至军区的纪录。这种跨越对于他来说,无疑是凤凰涅?。
但我更为关注的,还是他的一次例外。那是最新型坦克列装后的“第一炮”,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可贾元友首发竟然脱靶了。没有人总是百发百中,但由于是贾元友,现场气氛为他打上了问号。
其他人回到营房,贾元友却在坦克里没出来。5个小时过去,贾元友走出坦克,交出写得满满的8页纸。上面的几十条设问,远远没有局限在自己操作失误的教训上,而是一步步进行深刻的探讨和归纳,目光直指如何发挥信息化装备性能的深远领域。
坦克里的300分钟,他全力突击,试图穷尽那1发炮弹包含的所有可能。很明显,他根本没经历失利后的煎熬、恼怒、焦躁。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在挫折处停留,他跨越技术、挫折和迷茫。没人要求他这样做,由一发炮弹萌发的高度自觉,不是源自对使命的担当,又能是什么?
采访期间,我参加了部队的一次集会。几千人的会场静如平湖。而当歌声响起:准备好了吗?士兵兄弟们,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整齐洪亮的歌声,犹如山呼海啸,震撼着在场每一个人,不仅是歌声,还有充满着血性的歌词。那一刻,我感受到的是力量在迸发,青春在激扬,使命在召唤!
这是贾元友最爱唱的一首军歌,叫《当那一天来临》。我问贾元友,“那一天”是哪一天?他说,自从穿上军装,每一天都是“那一天”!
(照片均由解放军报记者 冯凯旋摄)